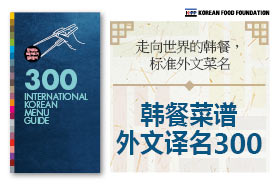- 余永定,前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院院长
有人说今天的产能过剩来自过去的过度投资。也有人认为产能过剩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。政府的观点似乎是两者的折中。一方面,当局要求数千家公司削减产能。另一方面,政府引入了一些“迷你刺激”措施,比如“微型企业”免除营业税和销售税、要求银行增加出口企业贷款等。
当局的官方口径是中国的增长模式需要减少投资、增加消费。但并非所有中国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一点。他们认为资本存量是增长的关键因素,而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相对发达国家仍然很低,这意味着未来投资空间很大。
诚然,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,而赶超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要求中国必须在长期增加资本存量。但要紧的不是资本存量的规模,甚至也不是投资水平;要紧的是投资的增长率,几十年来这一数字大大高于GDP增长率。
根据官方统计数字,中国的投资率已接近GDP的50%。拜吸收约束所赐,资本效率随着资本规模的增加而稳步下降。如果把飞速增长的投资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考虑在内,中国的资本效率还会更低。
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亚于实体资本和劳动。如果资源配置向实体资本的倾斜以破坏人力资本积累为代价——而后者又是充分消费的不可或缺的条件——经济增长就更有可能放缓而不是加快。因此,中国应该降低投资增长率,提高消费增长率,让投资率在更加可持续的水平上稳定下来。
当然,说中国的产能过剩反映的是有效需求的不足也不是完全错误的。但有效需求来自何处?
在这方面,中国钢铁业再次提供了很好的例子。尽管中国在钢生产方面并无比较优势,但仍建设了大约一千家钢铁厂,产出占了全球总产量的半壁江山。早在2004年,中国政府就试图降温过度投资;但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所带来的强劲需求,产出仍然增长迅猛,从当年的3亿吨增加到2012年的10亿吨。
中国的投资大体可分为三块:制造业、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。2008年底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顶峰时,经济刺激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提升维持了产出增长。2010年,房地产开发投资取代了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。如今,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都是中国增长的重要推动力。
中国确实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——特别是在电力和水电、交通和通信方面。但投资节奏必须充分考虑金融约束。更重要的是,中国可以也应该更多地投资学校、医院、养老院等社会基础设施。
但房地产投资则是另一回事。很难判断中国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以及破灭时间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:中国在房地产开发上已经投资得太多了。
中国的人均收入不到6000美元,但中国房屋自有率高达90%左右,而美国还不到70%。人均住房面积为32.9平米,而香港中位家庭住房面积才刚刚达到48平米。中国有696家五星级饭店,另有500家在建。在建的十座最高建筑中有五座位于中国。在我看来这只能用疯狂来形容。
中国经济正在被房地产投资绑架。一方面,中国不应该通过保持房地产投资的高增长率来解决产能过剩。社会住房项目投资值得欢迎,但目前占GDP高达10—13%的房地产投资已经显得太高。另一方面,如果房地产投资增长回落,产能过生就无法消除。这一两难凸显出中国所面临的结构性调整挑战——也应该让投资者保持谨慎。
总而言之,有两点值得警惕。首先,与其他投资类型不同,房地产投资并不增加生产性资本存量。房子和高价耐久消费品之间并无根本不同。其次,在中国的统计数据中,总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显著高于总资本形成增长率。这表明固定投资的增长率数据可能夸大了资本存量积累的速度。因此,尽管中国政府应该坚决地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,但动作必须非常谨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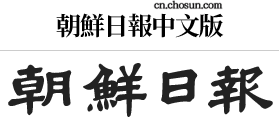



.jpg)
.jpg)
.jpg)

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.jpg)